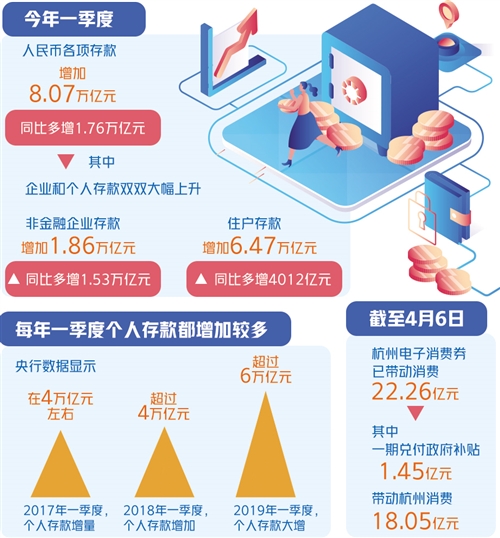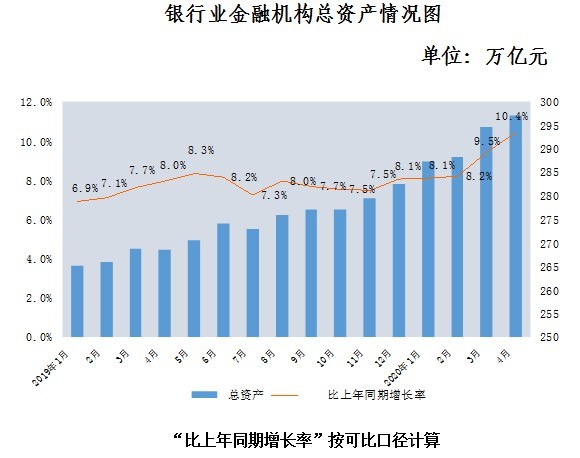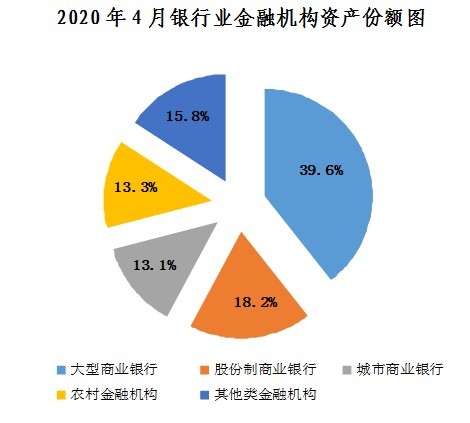這些天來�,阿炳的《二泉映月》一直在我心頭縈繞���。那繞梁多日不絕于耳的如泣如訴的輕吟���;那悲悲戚戚�����、哀哀怨怨��、凄厲欲絕的哭訴�����;那無奈��,那嘆息�,那詰問�!無一不撞擊著我的心靈��,刺激著我的靈魂���。使我聯(lián)想起曾經(jīng)銘刻在我的記憶里阿炳的生活情境:大雪象鵝毛似的飄下來���,凄涼哀怨的二胡聲,從街頭傳來……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媼用一根小竹竿牽著一個瞎子在公園路上從東向西蹣跚而來��,在慘淡的燈光下,依稀認(rèn)得是阿炳夫婦����。阿炳用右脅夾著小竹竿,背上背著一把琵琶��,二胡掛在左肩�,咿咿嗚嗚地拉著,在淅淅瘋瘋的飛雪中��,發(fā)出凄厲欲絕的裊裊之音��。
是的�����,阿炳生活在祖國經(jīng)歷了幾十年戰(zhàn)爭洗禮的動蕩年代����,國家和人民積弱積貧,物資極度匱乏����,生活極度困苦。他的悲慘既是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他的苦難有著深重的時代烙印��。
南方的春天�,是個多雨的時節(jié),滂沱大雨說來就來��,而且不像夏天的雨來得快去得快�,一下就是半天一天,整個地面和空氣都是潮濕的���,這幾天來就一直下著大雨��,只是有時大有時小一些罷了�。早幾天的一個傍晚�,我從門前的大路通過,當(dāng)時天空像灶上一層薄紗���,灰灰蒙蒙�,陰沉晦暗�����,傾盤大雨飛瀉而下�,雨點打在我的傘上,透過傘布�,下著毛毛細(xì)雨淋濕了我的頭發(fā)和衣裳,步行50米開外的距離�����,我離地一尺有余的裙擺打得透濕�。馬路中央,一個赤裸著上身���,雙腿已經(jīng)截肢的男人像朝圣的信徒一樣完全匍匐在一個有著四個滾珠的長方形木板上���,我看著他熟練的用左右手輪流擊打著大地“行走”,像游泳的運動員�,動作是那樣嫻熟,那樣有力�����。汽車的喇叭聲在催促他��,他為了躲避汽車����,躲避雨水,奮力的在地上劃著,不知要往哪里去��?也不知他能往哪里去��?看著他在地上艱難的滑行�����,司機從他身邊一溜煙沖過�����,濺起一浪又一浪水花�����,打在他赤裸著的身上����,沒有司機停下來給他讓路。在他的頭頂和肩膀上方的位置�����,還有一個用鐵棍焊接的長方形的架子����,他的身體就被夾在那個小架子中間,幾乎不能動彈���,要進(jìn)到那個架子里還需要他人的幫助����,因為架子太小他不能自己自如的翻動自己的身體����。架子上放著一個音箱和一個乞討盛錢的盒子,音箱中飄出的是阿炳《二泉映月》的二胡聲�。音箱音量很大很大,他所到之處�����,即便是嘩啦啦的雨水聲也掩蓋不了這個哀鳴聲����。我想,這是他的哭訴聲�,這雨水就是他的淚水。他飽含苦難的身軀經(jīng)受的折磨和他痛苦的心靈受到的踐踏有什么區(qū)別����?
阿炳用他那優(yōu)美的旋律傾訴自己傷感和楚痛�,發(fā)泄對坎坷命運的憤懣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樂曲流暢婉轉(zhuǎn)����,意境深邃���,卻掩不住傷感愴涼的情緒和昂揚憤慨之情���。
他沒有阿炳的才情,沒有自己獨特的表達(dá)方式�����。然而����,他的痛苦是否有過之而無不及呢?他如果有適度的保障是否可以在這種風(fēng)雨飄搖的惡劣天氣能安心的遮風(fēng)避雨呢��?是誰造成了他的截肢��,我們都不得而知。但是否也該有人為弱勢群體服務(wù)對弱勢群體負(fù)責(zé)呢�����?如果給他一張輪椅����,他是否可以不用像牲畜一樣活著�����,在地上爬呢���?雖然不能站起來��,至少他的手是健全的��,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難道非要這樣討生活嗎���?
這些天以來�,我陷入深深的自責(zé)自省中�����,我當(dāng)時明明有幫他撐一下傘的念頭,卻怕他早被無情冷漠的心摧毀的自尊心受傷害而誤解我的善意����,又怕旁人異樣的目光刺痛我脆弱的自尊。我明明看見他都已經(jīng)趴在地上了還不拉他一把��,我怎么這么冷酷無情�?我如果撐傘送他一程,給他遮一下風(fēng)擋一下雨����,不是給他冰冷的心一絲溫暖嗎?我悲天憫人的心哪兒去了�����?他不是我們同類嗎����,人類的同情心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看到情此景�、聽到此聲此曲的人們心中是否會有強烈的震顫?我仿佛聽到遠(yuǎn)處傳來純潔少年爽朗的笑聲����,漸漸的�,漸漸地變成了嗚嗚哭泣聲�,這是來自心底的呻吟,是對靈魂的拷問和救贖之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