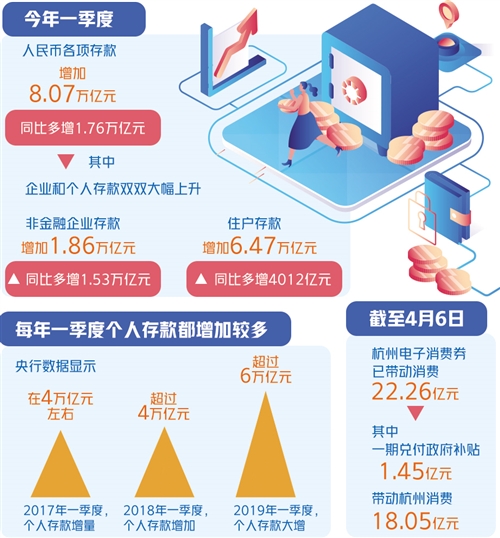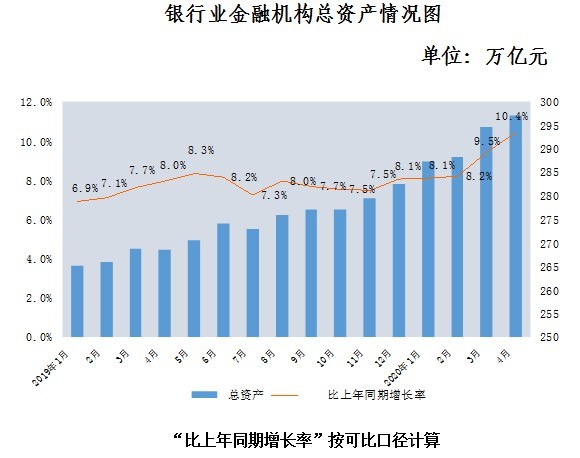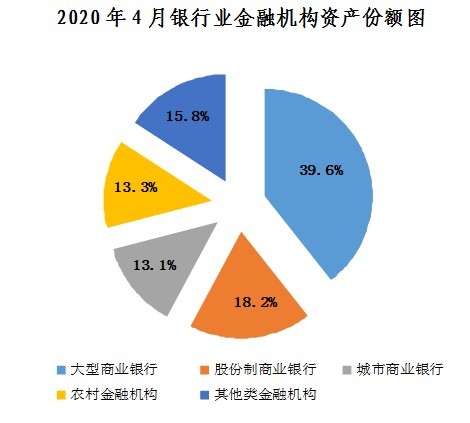連綿數(shù)日的大雨總算是歇了口氣,此時已近中秋�,晴空是一碧萬頃�����,每日趁著微風(fēng)出門��,涼爽得好似騰云�����。一到傍晚���,溫暖的霞光給整個城市鍍上一層金邊���,日子仿佛也慵懶起來,直教人憶起往昔�����。
我的幼年時期過得自由無憂,卻總不太平�。那時我隨奶奶生活在鄉(xiāng)下,剪短發(fā)��,瘦瘦小小�,每日跟著男孩子們“上躥下跳”、“飛檐走壁”��,山溝里撈魚����,翻越山頭摘果子都是家常便飯,時常曬得黢黑�,又帶一身傷疤,站在男娃堆里是分辨不出的��。然而�����,城市里那些好玩的����、好吃的,我都是沒見過的���。后來到了入學(xué)的年紀��,父母親就接了我去城里�。野孩子進城,哪能一下就收了心���?

記憶里的老師們都是嚴肅形象����。我愛語文�����,小學(xué)的班主任就是語文老師�,姓張�,留一頭長發(fā),皮膚很白���,厚厚的鏡片后面是一雙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在記憶深刻的眾多老師里����,我最該感謝她。與同齡人不同����,在學(xué)前班預(yù)備了兩年��,我就進入了小學(xué)課堂����。父母認為我年紀小,生怕我在學(xué)校受了欺負�,叮囑姐姐要照顧我,不曾想�����,我才是那個班級里的“小霸王”�。上課時偷吃零嘴,下課了往小女生的桌兜里扔小石子��,體育課女生們聚在一起跳皮筋���、踢毽子�����,也不乏我搗亂的身影��。于是其他任課老師向張老師訴說我的斑斑劣跡����,同學(xué)們也告我的狀,一時間�����,年幼的我好像成為了眾矢之的�����。面對即將到來的責(zé)備乃至所有學(xué)生都畏懼的終極懲罰——“叫家長”�,我也是十分懼怕的����。不料張老師卻出其不意,直到小學(xué)畢業(yè)�����,她也沒有在課堂上批評過我,更沒有在任何一場家長會結(jié)束后跟我的父母說些“悄悄話”�����。只是在以后的語文課上���,多了幾次提問我的手勢��;那時初學(xué)寫字����,張老師總夸我寫得好�;自習(xí)課講評作業(yè),張老師鼓勵我在班里朗讀自己的寫話���,并發(fā)動同學(xué)們?yōu)槲夜恼?hellip;…彼時只當(dāng)老師被我表里不一的偽裝蒙在鼓里���,如今回憶起來,那雙鏡片后無比犀利的眼睛��,怎么會被僅有幾歲的自己蒙蔽呢�����?
張老師陪伴了我的整個小學(xué)時期,猶記得越臨近畢業(yè)��,我越是生出對她的恐懼感:恐懼自己的進步不夠��,恐懼自己辜負了張老師的期望���,也恐懼自此以后�����,再沒有一位看似嚴厲得不近人情���、實際溫柔到骨子里的語文老師用自己的睿智與閱歷,融化一個少年因為來到陌生的環(huán)境里陡生抵觸而變得頑劣冰冷的心�����。
我的啟蒙老師��,張亞琴老師���,而今也該年過半百了。時光把我送到了二十三歲的階梯上����,想到您����,我仿佛依然還是那個半大的皮孩子�����,要感謝您的溫柔智慧與不曾放棄����,在我小小的童年記憶里刻上難以磨滅的一筆,為我的一生畫上了光彩奪目的起始符�����。咫尺千里�,師恩似海,學(xué)生在遠方祝愿老師身體健康���,平安順遂�,一切都好��!